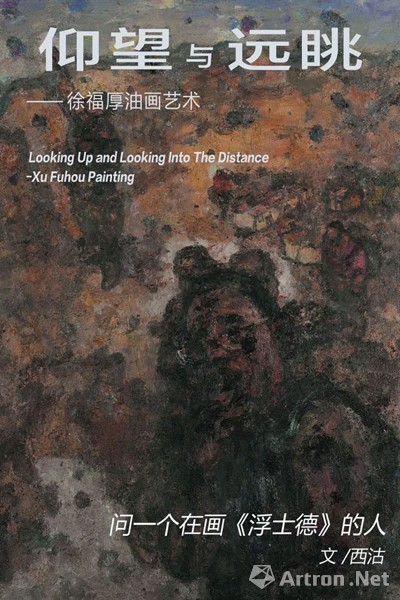
问一个在画《浮士德》的人
西沽
关于古典精神
Q:描述关于你较早时期的绘画工作,用古典绘画这种说法,在风格和技巧方面似乎有些接近,但并不能中肯;如用古典精神来描述它,则需要相对准确的定义,譬如我们谈到的古典精神,是不是就是指向了文艺复兴,以及它所宣称复兴的那种古代艺术?初期你的绘画可否说是遥远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A:当然,最初的诱发点依然是古典绘画。绘画语言方面的影响来自提香、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鲁本斯、安格尔等等,然而在风格意义上,我的绘画又并非全然古典的。那个年代大家对风格的定义有些粗糙,仿佛细腻并带有怀旧意味的就是古典绘画,我最初就对此有所警惕。
只是我一直有所自觉,那是对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的向往。这其中既有艺术方向上的选择,也来源于个人生命历程以及当时与社会生活之际的精神历险。对这种向往的探讨,竟一直持续到现在,涵盖了我大半生的工作。如今我可以约略谈谈这是什么了。
虽然所有的概括都有不精确的可能,我仍然把它定义为“古典”的精神。就像人类在与悲剧命运搏斗的过程中油然而生的豪迈之情,人类古往今来对于正义、崇高的追寻,这些与温克尔曼意义上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存在某种方面的共通之处,这是我所认同的古典精神,除此之外我还没有找到更为接近的概念。

《致歌德》 徐福厚 210×480cm 2019
Q:文艺复兴艺术更多的是出自对希腊、罗马的强大想象力。也即是说,那个古典是在对古代事实未必比现代人更清楚的条件下重新构想的。因此文艺复兴在另一方面开启了现代性。
你后期的绘画中能够反映出这种构想力。在你尝试定义的古典精神中,也渗透着显而易见的现代因素。其实你的书架上除画册外,几乎没有关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的人文著作,反而当代的东西更多,有部分更接近中国80年代的现代思潮。
A:是的,80年代真有先锋的气象,现代性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甚至政治的某些层面,这种文化冲击到目前为止都令人惊异。八五新潮的时候我在武汉,每个人都写诗啊,当然还看哲学书。80年代时候初读王朔的小说,看着那些对虚伪崇高的反讽,可以读到面红耳赤,“若有芒刺在背”。那时候也听崔健,记得他的小号从背景中升起,犹如人群之中游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的东西,直接并且有力。一时之间,这些东西夹杂着思路出奇的当代艺术,扑面而来,撬动着我的思考,让我不禁自疑。
我常对学生讲,刘小东、崔健、王朔各自从艺术的不同门类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世界,照亮了中国人在现代性面前心灵遭际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性肇始的里程碑和分水岭。中国现代艺术应该从刘小东、崔健、王朔开始。不像西方现代艺术从波特莱尔和塞尚开始。这是东西方文明进程的事,我如是想,不知是否准确。
回过头看,那一时的文化热潮与照亮人类若干世纪的伟大思潮当然不能同日而语:达芬奇照亮人类历史五百年直至永远。塞尚照亮三百年直至永远,但分水岭的意义是存在的。

《致歌德》 局部之一
Q:80年代知识人的阅读往往非常驳杂,除了诗歌、小说外,譬如哲学书,你也可以认为它与你的工作基本不相干,但是几乎人人都在看。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是本土文化新锐文艺,另一方面是一些译介来的经典哲学,仿佛构成了你那时思辨的催化剂。我猜想那个时候,可能每个人都在设想历史、当代和未来,哪些是变动的,哪些是不变的,道路在哪里?我甚至莫名其妙感到你的《若木》与《陈述》,有这方面的强烈象征。个人的选择在那个有共同阅读经验的时代开始分化,变得不同了。让人纪念的年代。
A:我那时候确实读到了些对我来说是“新”的东西,歌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等。这些书当然有纯粹哲学的艰涩读法、有美学的读法,除此之外有所谓东方的生命哲学的读法,西方叫做诗化哲学。
我吸收了西方现代哲学中,诗化哲学的成果。这些著作激起了我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我一直说现代性是个双刃剑,它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文化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炮制了前所未有的极多幻象。我进而想到人类的悲壮命运,不止体现于古典史诗中,同样在于面对现代性的复杂局面中。
威廉·福克纳说到,人类是唯一能在历史上留下声音的生物,他们用自己的理性精神传递着他们一代代积累的高尚感情,比如正义、理想、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同情之心和怜悯之心,以及爱。这些具有悲壮色彩的、永恒崇高的精神,正是我希望努力接近的古典精神。我并没有为日益变换的世界惊恐,我一直追问的是:对人类来说,不变的是什么?
假如我们站在更高处想,在人类精神历程的长河中,从荷马史诗到中世纪宗教艺术,到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令我惊异的是直到近现代思想家,甚至如尼采、海德格尔到福柯,他们精神宝库的最深层次中都有类似的精神倾向。这种精神倾向在人类思想历程中不断会被回望。
在我艺术从绘画到理论版图中,选择和借用了“古典精神”这个概念。如果必须给它一个定义,我冒着粗疏和片面的危险,那就是:人类在与悲剧命运的搏斗中油然而生的那种豪迈与庄严之感,以及在人类或个体生命进程中不得不经常回望的精神故乡。

《致歌德》 局部之二

《致歌德》 局部之三
Q:就我们谈到的而言,风格与思想之间、古典与当代之间,已经出现一种描述上的含混,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艺术家的刻意混淆?或者说得抽象一点,你所描述的这个古典的“存在”是否一直处在“时间”之中?
A:是理论而不是现象,构造了无限繁杂的蛛网,如今我们一劳永逸地把一种精神境界给出定义,已成为不可能。人类精神遗产的所有概念,每一个概念都是丰富的,某一个作者在某一个语境下使用了这个概念,是作者此时此地的选择,只是需要在学理上规定清楚。
至于古典精神,我当然意识得到这种含混。一方面,我在不断质疑这个所谓古典精神是否成立,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在事实上;另一方面,西方当代艺术、中国传统绘画,其实也一直哺育着这个我所伸张的精神,我并未感觉这些对于建设古典理想的异质性。它可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很当代的概念。
在我看来古今精神生活中的这个重大侧面,你想来想去,只有古典精神一词可以接近它。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中有过类似的追求,比如我的导师尚扬先生的巨大贡献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崇高与庄严立场。以及朝戈的艺术、丁方的艺术,都有各种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表述。在理论界曾有被称为“新人文精神”。但在我这里只有使用古典精神相对更接近其本质一些。

《百年孤独》 徐福厚 210×480cm 2019
Q:我是认同画如其人的,你画面上处理多重矛盾,映射出并非一味肯定的回答,我倒是认为反应了这种不断的自我质疑。在这种持续的推动力下,促成了我称之为追问的东西。在绘画中,追问成为了寓言。
A:是的,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关于古典精神追求,是建立在认真的学理思辨之上的选择,是在现代性面前在中国现代主义艺术大潮面前的一个选择。在此时毅然决然地返身而去,去演绎一个与古典精神相关的向往,并开始了大半生坚定的跋涉。

《百年孤独》 局部之一

《百年孤独》 局部之二
关于语言建设
A:当然我所描述的也从不单纯是思想,同样也关涉到绘画的语言。我曾经说过,艺术家在语言上作出些微贡献就是了不起的。
Q:的确如此。当今确实有一伙聪明人,以策划的视野,能够兴起波澜,事实上也推动了艺术。我想这是后现代的典型特质,它倾向取消作者,使得艺术家成为艺术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于是对绘画的描述形成双重言说,艺术家在乎一端,批评家在乎另一端。批评的确影响了艺术家,老实的作者也绝不会说:我并不在乎读者。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A:在第一本画册出来的时候,我总结过那是我为手工艺的辩护。现在我想这个态度基本没变。我对任何潮流、时势态度的前提是,我首先是个绘制者。

《三吏三别》 徐福厚 210×480cm 2019
Q:古典绘画的训练带给你什么?
A:在我早期绘画中,我试图去领会维纳斯、拉奥孔,去研究提香、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绘画中的秩序,还真的不是那套完备的优雅。这些画家所做的是对形的高强度运用,它使得那个形变得雍容博大了,他们的黑白高度归纳了,你可以在古典绘画中发现每一个边线、黑白、色彩的既对比又协调的最佳秩序。
以此眼力去观察世界,如果在绘画中能够描绘出对象世界的既对比又协调的陌生秩序,就接近于创造。
首先是结构。
倘若跳出古典画这个概念上似是而非的可疑阵营,不妨跨越时间,梳理出这样一些画家:弗朗西斯卡、维米尔、巴尔蒂斯、霍克尼。他们代表了画面外形结构的最高标准:维米尔的结构何其严谨。他呈现在画面上的那几个主要的形,都会形成一个特别严密的秩序,这个秩序有的是并列的,有的是冲突的,有的是协调的,但是你不可以改动它里边的任何微小的部分。这是一般意义的结构意识,这个意识随着巴尔蒂斯艺术引介,迅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被中国绘画界广泛接受和运用。
当然,我吸收了他们这些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画面当中的抽象结构,是建立在第一层图形逻辑之上,内在的另一层形式关系。这种结构关系就像钢筋中的水泥,撑在这个画面里。
最近我看到英国画家奥尔巴赫有过类似语言上追求,算是不约而同。当然呈现在画面上的不同,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在作品中读到。

《三吏三别》 局部之一
Q:在近期作品中越来越多的笔触叠加,使得外形的秩序感松动了,表面上看其实是对古典绘画的偏移,作品的形态让人想到黄宾虹。
A:是的,中国绘画自有在意象、精神化上的独特处。然而在黄宾虹之前,对线描的重视始终是主流,具象形态是显著的:山即是山,树即是树。黄宾虹的突出贡献是对不同的点、不同的线,不同层次的墨,不同的浓淡,的变化中堆积成一团气息,这些绘画语言表达他的精神指向。点与线面变成了独特的并具有精神化的东西。
在我的绘画中,我一部分吸收了这些成果。
在画面直接铺设了大概具象的外形,其中也运用了黄宾虹的方法,把人、山、天空编织变成为无数笔触,颜色,肌理,线条;这些笔触,颜色,肌理,线条各自是有表情的。与黄宾虹不同的是,我非常主动地吸收了西方现代绘画,因此笔触具有独立的气节,不仅如此,它们忽而潜伏在具象形态之中,忽而游离于具象形态之外。
Q:我是形式语言的坚定拥护者,但当我们反复提到秩序、关系的时候,反而有些担心,与之俱来的形式主义倾向。
A:这关乎形式主义的批判。若干年前与鲁虹的那个对话中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确实一直警惕这样的倾向。解决之道不外乎反复追问,借助于对美术史的了解、不断写生、以及近期对文化史的重绘。比如最近期的浮士德系列。

《三吏三别》 局部之二
关于叙事性
Q:艾略特曾说,人在二十五岁之后若尚欲继续从事写作,那么他对本国的、世界的历史与传统就必须有充分之理解。我知道你在画完《百年孤独》之后,又开始进行《浮士德》以及《三吏三别》等被你命名为《致敬·复述》系列的创作。这个意图是探讨西方的或古代的心智,抑或仅是一种对题材的焦虑?
A:我长期以来语言建设上的成果需要一个出口。一般认为日常的生活是平凡的,距离神圣很遥远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需要不断寻找题材,但这基本不构成任何焦虑。
我在这些经典作品中找到了演绎我这些精神理想和实现我语言建设成果的可能。无需去探究马尔克斯和哥徳的内心,更多是精神上的某种映照,使得我可以在名著文本的参照下,平行演绎着另一种可能。
歌德在八十三岁的时候完成了这个不朽巨著。他所描述的浮士德战胜了一系列诱惑:知识的诱惑、爱与美的诱惑、对统治者服务的诱惑,等等。我这里主要看中了人战胜一切诱惑,自我实现的不屈过程。尤其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这种体会越来越深:无论面对如何的惊涛骇浪,这种不屈不挠,是我认为人类最伟大的财富。
甚至是,战胜每一次生命的危机之后,归于平淡。而平淡之中又有不屈,这个不屈是什么,歌德没有说,这正是我理解的歌德的非凡之处。于我只有这个年龄才理解其深奥之处,若非如此,歌德的成就也还在《少年维特之烦恼》阶段。

《致波提切利》 徐福厚 200×450cm 2019
Q:你选取的两种作品看似遥远,然而都具有人类精神历险的意味。包括之前的《三吏》、《三别》,为什么偏爱史诗气质?
A:是的,百年孤独是关于一个古怪家族的史诗。所描述的那些人物,时而愚昧时而可爱,他们一百年间生活在那里,是坚韧可敬的,你会有时为他们的命运发笑,有时是感动。马尔克斯的的语言煞有介事,颇费细节。
我也在我的画里边,设计了好多的细节呀。我希望我的作品——当然我远远做不到——我希望是巨著。我仅仅有一个妄想,或者愿望:最少,它不是小品。我希望它里边有我自己设置的矛盾、冲突,起承转合,甚至像乐府法度中凤头,猪肚,豹尾这类要求。
这里的丰富当然不是原著的简单对应。这里将是我为视觉艺术的无穷魅力,矛盾的设置和推演……我相信我的目的就最少部分实现了。
我想说的是,绘画一定是视觉的。我相信,画中出现那些形象真的还是象布恩迪亚家族的人的,而展开冲突与融合有些马尔克斯丰富和剧烈。严格地追问,或更高的要求,也许缺少了马尔克斯的幽默和孤独,这也许还是在考验我的学养和功力吧。

《致波提切利》 局部之一
Q:记得我刚上大学不久,你就给我讲过,绘画作品最重要的是通过语言,而不是文学化的叙事语言感染观众或读者,你还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在作为小说不成功的地方在于他犯了一个“思想大于形象”的错误,它失去了小说“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段。这么多年来,你如何再次解释这个现象。
A:这似乎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最初的《若木》和《陈述》谁都看出了里面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之后我开始艰难的绘画语言的创造并取得了成果,就是说我绘画语言的表现力,大大地超越了叙事性,就是我已经成功的完成了“形象大于思想”的任务。甚至,即使《若木》和《陈述》还是形象大于思想的,就是绘画语言的魅力是大于叙事性的。那个语言建设时期代表作品如《大视野》系列,绘画语言更加纯粹一些。之后近期的《复述》系列,如《百年孤独》等仿佛文学性又回归了,文学性和叙事性内容更多了。但还是那一点,绘画语言的成就依然大于叙事的成就,这是肯定的。
再回到当下,参加周邻的创作,更透彻的比如纯抽象绘画,有成功范例,令人敬佩,但借助文学性,扩大作品的思想宽度和深度,为什么不可以。所有从前文学理论、艺术理论都一再被解构。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在此超越一步。我们还是去向作品本身追问,它会告诉我们。
顺便告诉你,当时我告诉你的道理是对的。那是那个时期文学理论的一个成果。

《致波提切利》 局部之二
Q:比起具象,我更有兴趣于“具体”,用你的话讲,叫做避免概念。记得你一位诗人朋友提到过希望你的绘画中更加关注“形而下”。对具体性的关注是一种中国独特的气质,在我们的思想史中,形而上的因素并不多见,反而总是在谈论“道在蝼蚁”,“洒扫应对进退”之类。我所好奇的是,在你绘画中的思辨气质与具体描绘之间,存不存在这种矛盾?
A:矛盾是好的作品理应具有的品质。你看得出来,我有一个思想方法,我总愿意把一些事物抽离成一个概念,然后再抽离、直到最高的概念。另一方面,我的写生活动正是想摆脱所谓的那个精神设置的那个预案,迫使自己关注形而下的当下,自己世界与周围的粗砺的质感。
再说到东方气质。确实,你看到我的思考里也有这层矛盾性。那么,我索性冒着简化的危险,再来区分一下:李泽厚讲过西方罪感文化与东方的乐感文化的区别,这算是文化背景;认识论上,西方重视科学的、实证的方式去理解、解释这个世界,而东方则是整体感悟式的。我年轻的时候,在读铃木大拙的《禅与精神分析》的时候留意到,他特别通俗地说明过这个道理。现在在美学范围,我可以我把那么丰富和庞杂、伟大的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高度概括为 “仰望”与“远眺”。

《复述-鲁本斯的马》 徐福厚 150×200cm 2017
Q:你说的让我想到了万神庙和中国园林,一个是站在空间的中心,向上张看那个代表形而上的孔洞;一个是巡游在时明时暗的园林中,目眺远山。
A:是的,我们再高度简化和概括一下,东方美学的基本特征,“仰望”可以认为认为是西方文化或者说西方美学的基本特征。而“远眺”则是东方文化及东方美学的基本特征。你想想吧,高居翰的那一系列书的名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不朽的林泉》等等,正好像是在为中国艺术的“远眺”特征做注解。
Q:你把将要举办的个展命名为《仰望与远眺》对于我,理解你的立场和理由。假如不熟悉你的读者,你不认为这个命题过于宏大么?
A:你问得好。
我想过这个问题。回过头来,第一,我是想让读者体会这个题目中两个动词的语感。“仰望”必定是人在仰望吧。“远眺”也必定是人在远眺吧。这里面重要的是作者,作者用作品表明在接受东西方伟大文明之前的立场和敬畏之心。
第二,我们和读者回到作品面前,当我们共同面对它们时候,只能感受作品本身,给予我们信息,作品所有元素和气息形成视觉成果和精神氛围会证明它。
2019·8·2-2019·8·11日
石家庄-杭州

Copyright Reserved 2000-2024 雅昌艺术网 版权所有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粤)B2-20030053广播电视制作经营许可证(粤)字第717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0792号粤ICP备17056390号-4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9402号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京公网安备 11011302000792号粤ICP备17056390号-4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1909402号互联网域名注册证书中国互联网举报中心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粤网文[2018]3670-1221号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总)网出证(粤)字第021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可信网站验证服务证书2012040503023850号